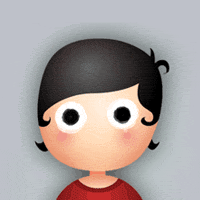元刻本《大广益会玉篇》及其他
《玉篇》是我国现存最早以楷书汉字为收字对象的字典,由南朝梁、陈间人顾野王编著,原书久淹无闻,今存日本的唐写本,或最为接近原本面貌,可惜仅存残卷。后代所通行者,乃业经唐人孙强增字、北宋大中祥符年间陈彭年等人重修之《大广益会玉篇》,该书宋本完帙亦早就难以寻觅,故昔之《四部丛刊》、今之《中华再造善本》,皆以元代刊刻之本影印流传;而当年涵芬楼借建德周氏藏本印入《四部丛刊》者实乃残缺之本,其卷十一至二十三配以明初刻本,说明彼时元刻足本已不易得,弥足珍贵。
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元刻本《大广益会玉篇》凡七部,除福建师范大学所藏八卷残本一时未能寓目者外,笔者于近日将国家图书馆所藏四部、上海图书馆所藏两部皆翻帘一过,包括博古斋本在内,粗看版式皆四周双边,黑口,半叶十二行,多为福建地区坊肆所刻,但无一版本相同。过去《善目》以为上图之莫棠旧藏十六卷残本(经部4423,上图书号797087)系元延右二年圆沙书院刻本,经与国图所藏圆沙书院本(经部4422,国图书号7319,即《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底本)相核,其版刻字体固自不同。这些本子之刊刻,各自皆偶有文字讹误,其文本也有所差异,如《玉篇广韵指南》,或有题“新编正误足注玉篇广韵指南”者;上图所藏另一足本(经部4427,上图书号858395-402),卷数、内容虽同,各卷编次则与其他诸本相异。但最须引起人们重视者,是某些版本的鉴定可能存在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元代至明前期刻书之业,福建地区可谓独领风骚,尤以书坊刻书最盛,但版本之学发展至今,专家学者们于此并未作过全面爬梳研究,对该时期建刻之特点面貌认识颇为模糊。倘若原本没有牌记,或牌记存在不确定性,人们往往会作出似是而非的鉴定。譬如《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有山东省图书馆所藏“元刻本”《广韵》(见《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二册00371号),实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明代永乐二十二年广成书堂刻本为同一版本,惟序后原有“永乐甲辰良月广成书堂新栞”之牌记,山东省馆藏本已被剜改。据余所知,珍贵名录之评审,人多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依据,但山东省馆藏本,《善目》著录为“明刻本”而非元本(见经部4822号)。意者《善目》定其为明刻本,系对该本牌记有所怀疑;而《珍贵名录》作元刻本,则以其字体类似元代福建地区刻书风气。这种刻书字体确实产生于元代,其根源唐楷,由建刻宋本起笔轻、落笔稍重之字体化出,但于起、落笔特别强调乃其特点,尤其是起笔,每呈现圆鈎或圆角状,颇为夸张,至明代前期,一直为福建刻书特别是书坊刻书所採用。过去治版本者讲版刻字体,于此疏于探究,多以元刻本流行赵松雪字体笼统言之,实际该字体与赵字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这种字体之流行,或者说这种版刻风格的形成,有一个渐变过程。元代初期的福建刻书,即便同一部书版,其字体并非皆呈如此面貌,建刻宋字尚占据一定版面,只是相较宋本字体偏软而已。迨至元代中期,宋本字体的遗意遂荡然无存,一式这种字体。但是,从元中期至明前期,这种字体也是有变化的,元中期时的字体尚具秀逸灵动之态,而元后期则略显板滞,至明前期则呈偏长规整之匠字,了无生趣(山东省图书馆的那部《广韵》便是如此)。当然,各时期所刻又有精粗高下之分,须细加比较,方能有所意会。
根据上述分析判断,所见诸本《大广益会玉篇》至少有两部系明版而非元代所刻:一为上图之莫棠旧藏残本,写刻颇劣,过去定作元刻,实因受客观条件限制,无法与他本比较。另一为国家图书馆藏詹氏进德堂刻本(经部4426,国图书号10506),其卷一末有“詹氏进德书堂重刊”刊记,或许国图另有一部明弘治五年詹氏进德堂刻本的缘故(经部4432,国图书号7968),因版刻不同,便将此本定为元刻,但其字体呆板,甚至较国图另藏两部明初刻本(经部4429、4430,国图书号7966、7320)有所不如。此外,该两部所谓元刻本与国图两部明初刻本之版式皆为粗黑口,这一特徵也是在鉴别元、明刻本时需要注意者。至于国图、上图其他没有牌记之元刻本,窃以为皆刊刻于元代后期,唯独博古斋本为元中期刻本,而且刻印较国图之延右二年圆沙书院本为佳,尤其是该本用质地颇为细洁之黄麻纸刷印,不特为元刻元印之凭据,较之其他用竹纸刷印之元刻本,其价值当更胜一筹。
由赏鉴一部元刻本而作一极为初步的个案研究,是想告诉人们,因受历史条件限制,前人编制目录往往是以自己的藏书与别家的目录进行校核,这种状况甚至到了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也未获根本改变,故所作的版本学研究只能是局部的、粗线条的。当今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老老实实进行版本个案研究,在掌握大量实物版本信息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完善鉴定版本方法,才能逐步攻克前人留下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