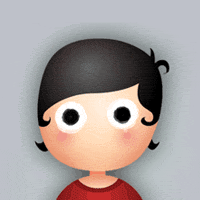痴情方许说红楼
周汝昌(1918—2012),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生于天津。燕京大学西语系、中文系研究院毕业。曾任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批终身研究员等。中国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著有《红楼小讲》《红楼梦新证》《曹雪芹的故事》《石头记会真》《书法艺术答问》《北斗京华》等。
周汝昌先生有一本面向普通读者讲论红学的书要付梓问世,出版社希望有人写一篇小序让读者对周先生的“特点与成就”有所了解。周先生把这一任务交付给我,是谬托知己的意思,我虽然有点诚惶诚恐,也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周先生写曹雪芹的传记时,曾以《孟子·万章下》中的一段话语为指归。这段话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那么,我们读周先生讲论红学的著作,作为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对周汝昌先生有所了解的确是大有裨益的。
周先生是1918年生人,也可以说是世纪老人了。他在青年时代本来是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学英语的,后来还在四川的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当过好几年教授英语的老师。可是,他从1947年起,就“一不小心,成了一个红学家”。1953年9月,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红学著作《〈红楼梦〉新证》。这本书近四十万字,对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的版本、脂砚斋的批语等有关阅读《红楼梦》的背景情况作了深入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成为胡适和俞平伯开创的“新红学”之集大成式的著作。这本书后来又不断充实完善,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再版时,已经成为八十万字的皇皇巨著了。此后50多年的风风雨雨里,周先生不倦不辍地从事红学和其他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的研究写作,特别是后来患眼疾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恒兀兀以穷年,不知老之将至。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二十册以上的学术著作,其中研究《红楼梦》的就有十五六部。
周先生的红学研究,第一个特点是其全面性或曰涵盖性。也就是说,他几乎涉足了红学研究的每一个具体领域,而且都十分深入,不是浅尝辄止或蜻蜓点水的那种“学术”。红学中的各个分支,都印有他的深深足迹。周先生在1981年给拙著《〈石头记〉探佚》写的序言中就提出了红学有根本性的四大分支的论点,即曹学、《石头记》版本研究、脂批研究和探佚学,是对《红楼梦》作思想哲学、审美艺术观照评论之前提和基础。意思是说《红楼梦》思想和艺术层面的辉煌只有建立在那四个分支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呈现。因此,周先生首先在那四个分支的建设上付出了巨大的精力。《红楼梦新证》的“集大成”意义也在这里。此外如关于《石头记》版本和脂批的《〈石头记〉鉴真》(《〈红楼梦〉真貌》)《〈红楼梦〉真本》,关于大观园原型考察的《恭王府考》《恭王府与〈红楼梦〉》(《〈红楼〉访真—大观园与恭王府》),关于曹雪芹生平的《曹雪芹小传》《曹雪芹新传》《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关于探佚的《〈红楼梦〉的真故事》等,就是对各个分支所作的专题性研究。可以说,每一种书都体现了迄今为止该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
这四个分支的研究奠定了红学的坚实地基,虽然它们本身也是可以单独欣赏流连的美妙风景线,但更本质的意义却是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在上面搭建起思想和艺术(哲学和审美)的“七宝楼台”。周先生写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两本大著就是矗立在那四个分支地基上光芒四射的“宝塔尖”。当然在周先生的其他著作中其实早已经有许多关于《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讲论赏会,不过没有这两本书集中和专门罢了。这也说明,四大分支的基础研究和思想及艺术的评断鉴赏其实是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我们分开来另立名目不过是如佛家所说“方便法门”而已。
周先生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那四个分支研究呢?为什么不“就文本谈文本”呢?这就是红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关键所在。原来曹雪芹的原著只传下了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是另外的人所续写的。这就产生了“两种《红楼梦》”这一学术难题。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都不严格区分原著与续书而泛谈所谓《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造成了《红楼梦》评论的庸俗,红学研究的迟滞。要破除这种历史困窘,要解决这一学术难题,该从何处入手?周先生老马识途,心明眼亮,一针见血地指出唯一的门径就是把那四个分支的基础研究搞深搞透。因此,周先生说那四个分支是红学的重镇,并不是要否定《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研究,而恰恰是要通过那四个分支研究以区分出两种《红楼梦》两种不同的思想和艺术境界。这可以说是周先生全部红学研究之核心的核心,也可以说是周先生红学研究的第二个特点,即文化性特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区分了“两种《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寻根究底,最后就归结到中华文化本身的特质和其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纠缠。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精粹部分的卓越体现,又是对中华文化负面因素的反思和扬弃。用周先生的话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是进入中华文化的“一把总钥匙”。而后四十回续书,则在根本的理念意向和艺术精神方面歪曲篡变了曹雪芹的原著。当然后四十回在鼓舞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恋爱及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封建家族和官场的黑暗方面也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这与曹雪芹原著要表现的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灵性价值之高远追求,以及审美意度之戛戛独造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用天壤之别、南辕北辙这样的字眼是并不过分的。周先生从一开始进入《红楼梦》,就盯紧、抓住这个红学中的“死结”,毫不放松,孜孜矻矻,锲而不舍,从各个层面、角度来研究、论述、分析、讲说,使这个问题逐步得到彻底清理,而其终极目的,就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揭示和解决,使中华文化的深刻和曹雪芹的伟大昭然于天下。这也就是为什么周先生又说红学是中华文化之学,是“新国学”的原因所在。
由于问题的复杂性、解决的艰难性和过程的长期性,周先生因此承受了许多误解,所幸“真理愈辩愈明”,到了21世纪,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红楼梦》的读者开始理解和接受周先生的这种“文化性”红学了。一些人往往从表面上看问题,说周先生是一个“考证派”红学家,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应该说周先生是“文化思想派”红学的代表才更恰如其分。“新红学”的两位开山祖师,胡适主要是在“历史考证”的层面作了开拓,俞平伯则在“文学考证”的层面成绩突出。也就是说,胡适的贡献主要在作者和版本的认定方面开端引绪,俞平伯则对《红楼梦》的艺术性作了相当深入的探索,但他们对《红楼梦》的思想文化性价值或比较隔膜,或理解得还不够透彻。周汝昌则不仅对历史背景和文本艺术的考证及研究作了更深入广泛的拓展,而且特别关注《红楼梦》的思想性,关注“两种《红楼梦》”的精神气质差异,并把这一问题的观照和探讨提升到了文化的层次,从而使《红楼梦》的阅读和研究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理、扬弃、承续、发展,与当下中国人性灵的陶冶、思想的启沃和精神的寄托发生更直接更深刻的关系。
周先生红学研究的第三个特点,可以说是“文采风流”。正如周先生说曹雪芹是“文采风流第一人”,也可以引申说《红楼梦》是“文采风流第一书”。要把这文采风流第一书和文采风流第一人的本质、要义、精彩阐释出来,评赏估价到位,这个讲说者和评赏人当然也得有一点“文采风流”的素质和特点了,这是不言自明的事。简明扼要地说,周先生的红学著述具有考据、义理、辞章三者咸备的特色,考据是“真”和“史”,义理是“善”和“哲”,辞章是“美”和“文”,也就是具有真、善、美或文、史、哲三者结合而相得益彰的品质。这真是十分难得,能达到这一境界,在今天的学术界文化界,不说凤毛麟角,也是百不得一。周先生能臻此胜境,当然既有他的天赋资禀,也和他长期的修养历练分不开。周先生是一个十分聪颖的人,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在诗词和随笔的创作、外文的翻译、书法艺术的操习,乃至音乐吹弹、戏曲表演甚至梅花大鼓词的写作和欣赏等多个方面,都有不同寻常的修养和建树,更不必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如唐宋诗词、民俗工艺等方面的研究讲解了。周先生是学者,是诗人,是文章家、书法家,尤其善于作创造性的感悟思索,这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合力”,体现在《红楼梦》研究上,就特别能发抉彰显出《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精、气、神,其底蕴内涵、文情艺韵。这其间的“理路”和“张力”也很容易了解,因为《红楼梦》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和“一条主脉”,曹雪芹本来就是一位集诗人、哲人、艺术家和小说家于一身的中华文化的“文曲星”。
万派归源,可以说周先生的红学研究是中华文化精义的一种学术实现。那么这种中华文化的精义又是什么?《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有一段话这样说:“试看这一切,即我上文所论述的晋贤的‘痴’,晏小山的‘四反’,张宗子的‘七不可解’,以至雪芹的‘作者痴’,宝玉的‘痴狂’‘疯傻’,悉皆相通相贯,而这种类型的人物,即是雪芹所说的‘正邪两赋而来之人’……是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英。他们的头脑与心灵,学识与修养,显然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可宝贵的精华部分。迨至清代雍乾之世,产生了曹雪芹,写出了贾宝玉,于是这一条民族文化的大脉络,愈加分明,其造诣亦愈加崇伟。”这种“中华文化上的异彩”就是“正邪两赋”,就是“痴”。而周先生的红学研究,也正好十分有趣地体现了这种“痴”,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锋镝犹加,痴情未已”。有了这种“痴”,才一往情深,才无怨无悔,才生慧心,具慧眼,成慧业,造就出一代红学大师。周先生的这册《红楼小讲》,我只看到了目录,但已经感到是能够引领普通读者进入《红楼梦》真境圣境的宝筏南针,能够让读者对曹雪芹的“痴”所体现的中华文化之精义初尝滋味。我曾经赋赠周先生一组绝句,就录下其中之一作为本文的“点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