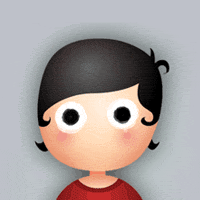具先锋文学气质的新史诗
南都讯 记者周佩文 “红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文学性新标高。”“史诗性作品并非一定得有很长的篇幅。认为史诗型写作必须无限度地拉长篇幅,这其实是一个误解。”“这是在文体上的突破,这种革命性和创新性很突出。”“作者创造了一种新文体。”……6月26日,在“长征解密与文本解码――《乌江引》广州研讨分享活动”中,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和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等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乌江引》的文体展开热烈讨论。
专家们一致认为,这部“伟大长征精神崭新书写”之作具有超出红色题材的重要文学价值。《乌江引》既是长征密电全新解密,也是史诗叙事的文体创新。作为打破纪实与虚构界限的小说力作,这部作品在主题、结构、叙事、人称和语言诸方面的现代性探索弥足称道。这是一部能够真正走向读者的可读性很强的作品,也将是一部具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文学精品。就叙事艺术和美学品质而言,这个文本也是“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这样的文本创新亦可给更多写作者以有益的启示。
作家庞贝的长篇新著《乌江引》今年3月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首印高达5万册。《人民文学》同步刊发,《当代长篇小说》迅即转载。这部作品面世之后迅速荣登“中国好书”“第一季度影响力图书”等十几个权威月榜或季榜,也迅速登上当当网新书热销榜等榜单。在广大读者中引发热情关注的同时,这部作品在党政军界、史学界和文学界也获得了积极反响。
在本次研讨分享活动中,与会专家从文学原创性方面对这部“长征解密”之作进行了“文本解码”。
《乌江引》的“新”来自作家的天赋和才情
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从“作者”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感受:首先,“《乌江引》给人的印象非常新,它在写法上、结构上、表现方法上都显示一种很新鲜的,是我们以前看其他小说没有的经验。……这与作家庞贝本身的天赋和才情有关。”其次,长征是人类的伟大史诗,但史诗怎么写?很多人的想法是跨度很大,时间要拉得很长,把整段历史写出来。但是《乌江引》仅仅用21万字就把长征写出来了。“庞贝的办法就是把这段战争风云收拢到二局这几个人身上,通过这几个人来反映这段历史,它赢得了创作需要的艺术运作空间,但是又反映了这段时间,所以就使这本书带有史诗的品格。”第三是小说的语言。“庞贝本身有古代汉语的根底,又有外语的根底,更有现代汉语的根底,所以这本书的语言很有特色,这几种修养都体现在里面。它不是简单的白话文,他能模仿那段时间那些人文的讲话、对话等等,他都能模仿,所以他在推动白话文雅化方面也有值得我们重视的成果。”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则在发言中指出,《乌江引》成功的重要原因首先在于作家做案头工作,做资料调查、田野调查、后人的访问,这种案头工作为小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物质基础。“小说写出来之后,它和读者之间是有一种阅读的契约的,我之所以还愿意读下去的原因就是我相信你所写的东西是真的。而这个真实的契约最重要的基础其实是物质基础,你要写的人物,包括器物、风俗、事件,甚至连风景、建筑,吃什么、喝什么要有一个实证的背景,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实证的背景我们就无法相信你所写的是真的。”其次,作家对已掌握的这些资料的选择,对这些资料的删削,能看得出来其下了苦功。“我觉得所有的这些资料工作、案头工作和对资料的遴选决定了他这样一部作品的基本风格,一方面有信任感,另一方面又觉得没有完全湮淹没在所谓的史实当中。”第三,这部小说选择纪实与虚构两条线,其实也是为自己腾挪一些文学想象的空间出来。破译这个行当里面固然有曾希圣这样一些所谓的功勋累累的,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也有一些无名者。《侧影》部分其实是虚构性的,也设置了一些人物,这些作为参照,为人的丰富性跟复杂性拓展了空间。
“《乌江引》立体呈现了伟大征程史诗般的庄重和壮阔。”《人民文学》杂志刊发此作时的卷首语中曾有如此表述。长征是一部人类精神的伟大史诗,《乌江引》是向这部伟大史诗的致敬之作,也是这部史诗的“副歌”。作为长篇小说,《乌江引》本身就是一种史诗新文体。在本次研讨活动中,专家们就史诗的概念和史诗性长篇小说形式的现代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红军长征是一部人类史诗,而荷马史诗写的也是古希腊人的远征,这二者应有某种精神气质的相似,一种人类意志力的显示。荷马的《奥德赛》是一种史诗,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是一种史诗,基于这样的认知,《乌江引》作者无疑是找到一种史诗的新形式。假如说《尤利西斯》是一部现代史诗,那么《乌江引》显然也是具有某种现代性,当然,这是与《尤利西斯》不一样的形式。今年适逢《尤利西斯》面世100周年,《尤利西斯》本身就有荷马史诗的原型和母题,因此对于史诗文体现代性的这番探讨更显得饶有新意。
“这样一段革命秘史天然地具有传奇的色彩,往革命历史传奇的路子写本是顺理成章的,庞贝却没有选择这一路径。面对这一题材,他的态度是郑重的。在他眼中,这并非传奇,而是史诗。”青年评论家李德南在论坛发言时说,“通常说到史诗型的写作,很多人会认为,这样的作品需要有巨大的叙事体量。仿佛只有如此,才称得上是史诗。然而,在不少作品中,篇幅之长是通过注水的形式来达成的。在这样的语境中,《乌江引》在叙事上的慎重与简约,让我觉得特别可贵。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具有史诗色彩的历史题材,庞贝仅用了十几万字的篇幅予以呈现。这也说明了一点,史诗性作品并非一定得有很长的篇幅。认为史诗型写作必须无限度地拉长篇幅,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专家们认为,长篇小说的现代性,是一种艺术形式上更为讲究的、更为高级的呈现。这种“高级感”,就《乌江引》这部作品而言,就是这种“史诗般的庄重”,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感”。“与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叙事原则不同,今日革命文学写作应是一种现代性写作。与某些新历史主义小说也不同,《乌江引》绝无‘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纠偏。”广州市文学评论家协会主席申霞艳教授说,“史实与虚构之间的博弈,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这种博弈本身就构成一种巨大的张力。庞贝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以自己的小说智慧复活了一个智慧的群体。这使我想到以色列作家赫拉利的那个有名的说法:人类的想象力与信仰有关。《乌江引》这个叙事有一种特别的庄重感,而这也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温情记忆,一种动人心弦的力量,比如作品最后的那几行诗句。对于面对复杂时世的当今读者来说,这是一种很难得的感受。”